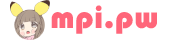自2014年6月以來,國際原油基准價布倫特油價從115美元�桶的高位上下跌,到2015年1月7日跌破50美元,降幅50%多,達到了自2009年以來的最低點。當前,歐佩克經過兩輪協調會,迄今未做出減產決定,近期油價下跌步伐恐難停止。這一事態反映了近年來國際能源形勢的新變化,也折射出中國外部能源環境的機遇與挑戰,中國應積極開展能源外交妥善應對。
國際能源形勢的新變化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提速,地緣政治深刻調整,全球能源供需總體平衡,國際油氣供應有向“買方市場”轉變的跡象,價格下行壓力增大。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能源市場上佔據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國能源安全的外部環境趨向相對寬鬆。
一、油氣供應相對充裕
隨著油氣勘探開發技術的進步、非傳統能源來源的增加及能效提高,全球能源形勢得到改善。據英國石油公司(BP)統計,2013年,全球石油、天然氣、煤炭產量分別增長0.6%、1.1%和0.8%,[1] 儲採比穩中有升,油氣供應相對充裕,人們對傳統化石能源枯竭的憂慮降低。預計從2012—2035年,世界一次能源產量年均增長率將保持在1.5%,與消費增長持平。[2] 與此同時,以中東、北美、俄羅斯、中亞為主的四大能源供應板塊更加清晰。其中,中東的石油和天然氣探明儲量分別佔據世界的47.9%和43.3%,石油和液化天然氣(LNG)出口分別佔世界總出口的34.9%、41.3%,保持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應中心地位。受益於頁岩氣開發技術突破和政策鼓勵,美國非常規能源的發展游刃有余,極大釋放了油氣生產和出口潛力,並帶動北美成為全球第二大能源生產區域。俄羅斯和中亞板塊仍是世界最大的能源盈余地區。俄2013年天然氣增產125億立方米,實現了世界最大的增產量,並仍是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國。此外,非洲、拉美等新興資源國的吸引力增強,隻不過囿於經濟發展狀況、基礎設施不足、資金和技術服務缺口等因素,其資源開發和煉廠產能的提高尚需一個過程。
二、能源消費重心加快“東移”
全球一次能源消費增長加速,增長率從2012年的1.8%增至2013年的2.3%,略低於近十年的平均水平2.5%。新興經濟體一次能源消費增長3.1%,成為穩定的能源需求增長源。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非經合組織國家吸納了世界石油出口的49.4%,其石油消費量佔世界的50.6%。亞太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成為73.2%的LNG出口目的地,其水電增量也佔到世界水電增量的78%。事實上,僅中國一國的能源需求就在2007年超過歐盟國家,2010年超過美國,2014年則有望超過整個北美。[3] 相比而言,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能源消費增長率為1.2%,以美國(2.9%)最為強勁,但歐盟、日本分別出現了-0.3%和-0.6%的增長,西班牙降幅最大,為-5%。能源消費重心“東移”,主要有兩方面的動因。一是西半球能源自給程度上升和歐美油氣進口觸頂,特別是發達國家得益於能效提高而出現石油消費下降,這為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增長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也促使傳統供應方更加積極地對接東方,尤以中東為甚。二是亞洲經濟增長勢頭強勁,需要持續增加的能源消費作為支撐,其龐大的能源市場容量成為各大能源產區激烈角逐的對象。俄羅斯、美國等傳統和新興的油氣生產國均日益將亞洲視為能源出口目的地。
三、能源結構難有實質性變化
頁岩氣、頁岩油和海上石油等非常規油氣產量的攀升,為全球油氣供給端注入了強心劑。在可預見的未來,能源結構仍將以化石能源為主。具體看,盡管石油佔全球能源消費的比重已連續14年出現下降,但實現了1.4%的增長,仍是世界主導能源。煤炭作為全球最便宜的電力來源,深受新興經濟體青睞,成為增長最快的化石燃料,並出現供過於求的趨勢。天然氣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地位繼續上升。預計,隨著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長,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會從當前的86.7%緩慢下降至2035年的81%。
面對嚴峻的能源和環境問題,世界各國均把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作為保障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共同出路。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水電、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發展迅速。2013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發電中的比重從五年前的2.7%增至5.3%。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從2011年的13%提升到18%﹔屆時,世界發電增量的二分之一將是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4] 然而,可再生能源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風電、光伏制造業產能過剩,以及因補貼政策調整導致的產業投資波動等問題。自2012年以來,全球新能源投資已經連續兩年負增長。[5] 短期內,可再生能源消費無論就其存量還是增量而言,均難撼動傳統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供應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
四、油價回落基本反映市場現實
此輪油價的大幅回落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世界經濟增長放緩,歐洲和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都低於預期,對石油需求不足。二是供求平衡出現變化。2013年以來,美國非常規石油以及加拿大油砂油彌補了此前由中東局勢動蕩引起的石油生產中斷和供應缺口,再加上伊朗和利比亞等國逐步恢復出口,石油供應開始進入充裕時代。三是沙特、科威特等歐佩克國家拒絕削減產量,以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喪失份額。外界普遍猜測,沙特等國樂見低油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原油產量的增長,以便將美國的新興油氣生產商擠出市場。此外,這一問題也涉及地緣政治利益,比如,美國政治評論家托馬斯•弗裡德曼指出,低油價是美國和沙特聯手導演的“陰謀”,以打破俄羅斯、伊朗的財政平衡,迫其破產。[6]
短期內,原油和燃料價格下跌對能源進口國而言是個利好消息,有利於降低能源進口成本和工業成本。但它也會造成能源經營風險,威脅到北美、巴西等地正在掀起的產油熱潮,並對資源國、產油國及出口國造成財政壓力。從長遠看,世界油氣供應的多元化和能源需求的多樣化趨勢客觀上有助於推動油價定位向市場理性回歸。在國際金融市場和地緣政治等其他條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供需基本面不會支持油價大幅向上波動。
中國能源安全的新挑戰
國際能源形勢變化預示著,一個相對寬鬆的能源市場環境正在確立,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且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達到58.1%和31.6%,[7] 今后仍將面臨能源需求壓力大、供給制約多、消費結構轉型緩慢、能源地緣政治關系復雜等諸多挑戰。
一、市場競爭更趨激烈
亞洲能源資源相對貧乏,而能源需求保持旺盛,並且嚴重依賴地區外能源供應。這決定了亞太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能源供應格局中的地位仍然較低。在中國周邊,除了北部相鄰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是能源淨出口國之外,其他鄰國基本都是能源淨進口國。例如日本、印度、韓國等均高度依賴中東的油氣供應。他們在國際能源市場上彼此競爭,不可避免地存在摩擦或沖突。中國在非洲和拉美等新興資源地區的能源活動也面臨大國競爭。由於地理鄰近和傳統紐帶,非洲石油出口的43.4%、LNG出口的44.5%及管道天然氣(PNG)出口的82%運往歐洲,中國所佔份額不大。西半球能源秩序則很早就被美國所主導。印度、日本、俄羅斯、伊朗等則基於各自的能源、商業及政治利益而提升與拉美國家的能源合作。總的看,由於石油供應主要來自地區之外,這涉及油氣供應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系狀況如何,是否願意以合理的市場價格向中國出售油氣,運輸過境國是否提供安全保障,以及來自其他油氣進口國的資源競爭等問題,必將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影響。
二、可持續發展需求上升
由於能源開發的環境和社會治理成本明顯,世界各國均主動在能源、環境和氣候領域向低碳路線靠攏。以美國為例,受益於頁岩氣開發以及天然氣替代煤炭的作用,其能源結構得到優化,溫室氣體排放量顯著下降,2012年時達到比2005年減排11.8%的水平。[8] 隨著國內油氣開採進入新一輪繁榮期,奧巴馬政府將努力對由此造成的環境問題進行規范,並可能在國際氣候談判上轉入主動地位。而中國仍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漲時期,不僅短期內難以改變高能耗的產業結構,且能源強度還會上升,再加上中國的能源結構特點是“富煤、缺油、少氣”和水力資源豐富,這對溫室氣體減排和經濟可持續發展非常不利。據BP統計,2013年,中國煤炭消費為19.33億噸油當量,相當於世界煤炭消費量的50.3%。同年,全球碳排放的最大來源也是中國,佔28%,對全球碳排放增量的貢獻則為58%。[9] 中國在煤炭消費量及污染排放方面所佔比重如此之高,使中國成為國際環保力量針對的一大目標,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承受的壓力上升。
三、能源地緣政治博弈復雜
地緣政治因素引發的能源價格波動和供應安全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從能源來源地看,中國對中東依賴高,前十大石油進口來源國中有六個都位於中東,中東局勢動蕩使中國對中東能源價格和供應安全的承受力十分脆弱。例如,中國與伊朗的能源關系就受到美國對伊朗制裁措施的明顯影響。從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看,自美國“重返”亞太以來,一些周邊國家就加大了與中國競爭能源資源的力度,高調對中國領土和領海進行挑舋,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更為復雜。例如,東亞的中國、日本、韓國同為能源消費大國,本可作為一個整體在同供應方議價、維護能源運輸安全方面形成合力,卻彼此矛盾深重,致使合作遇阻。從能源運輸通道看,中國石油進口通道過於單一,主要依賴海上,其中90%是外籍油輪運輸,且80%的石油進口需要通過馬六甲海峽。相關海域安全形勢會對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產生較大影響。此外,國際輿論總體上對中國能源“走出去”不利。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與中國存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其主流媒體常常炮制“中國能源威脅論”,蔑稱中國能源企業“走出去”是搞“資源殖民主義”,質疑中國石油公司因“國家背景”而開展不公平競爭,並擔心中國參加國際油氣資源的上下游活動會“侵蝕”美歐傳統勢力范圍。中國在維護能源利益的同時,還面臨著維護國家政治利益的重任。
中國能源外交的新機遇
隨著中國在國際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凸顯,能源問題已被提高到中國國家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來對待。[10] 中國應當立足於國內基礎,積極開展國際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降低和應對因海外油氣依賴而帶來的風險,不斷提高自身在國際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首先,樹立科學的能源安全觀。必須立足國內,增強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做出合理的能源戰略布局,明確科技創新方向,提供相關政策鼓勵和支持。有必要依靠技術進步,推進能源結構優化,控制煤炭消費總量,約束能源消費行為,確立節能優先的能源發展戰略。同時,應認識到能源依存是不可回避的戰略選擇,重視國際能源市場對於滿足能源需求、穩定能源供給的重要作用,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市場的開發和利用,“在開放格局中維護能源安全,掌握發展的主動權”。[11]
其次,擴大國際能源合作。利用好國際能源供應的多板塊格局,在市場佔有上更加多元,避免對單一賣方形成過度依賴,增加中國在能源市場上的選擇。對“走出去”戰略進行升級,以貿易和投資並重,開拓上下游各環節合作項目,注重資產質量和運營能力的提升。重視維護能源運輸通道安全,在已經實現的西北(中亞油氣)、西南(中緬油氣)、東北(中俄原油)和海上(來自中東、澳大利亞、拉美國家的船運油氣)等四大能源進口通道布局基礎上,考慮通過建立維護跨境管線安全的政府間機制、簽署保障境外管線安全的國際協定等方式,塑造能源利益共同體。
第三,開展積極的能源外交。一是加強與能源大國的合作。美國、俄羅斯、沙特等既是石油資源大國,也是石油生產和消費大國,在世界石油市場上佔有重要地位。歐洲、日本、伊朗等也對全球能源市場影響較大。中國應加強與重點國家的合作,進行政策對話,建立信息交流機制,推動能源技術引進。二是運籌周邊外交。應鞏固和加強周邊,重視挖掘就近供應渠道,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提出新的能源倡議,打造重點項目。三是維護海外投資利益。有必要通過國際法和國際經濟專業領域內的法律機制創新,建立海外投資利益保護常態機制,探索油氣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加強風險研究和預判。四是參與全球能源治理,包括推動形成區域性能源合作機制,變能源地緣政治為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合作關系。可聯合主要能源消費國,推動形成亞洲油氣進口國協調機制。也可聯合中亞、西亞等主要油氣生產國,建立區域油氣交易平台。此外,能源企業是中國前沿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成員,應鼓勵其不斷提高素質,加強管理透明度,提高工作和服務質量,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和制度規范,建立環境和社會效益報告制度,改善企業形象。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
[1]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4, p.8, p.22, p.32.為保持統計數據標准的統一,文中相關統計數據均源於BP年度統計年鑒,另作說明的除外。
[2] 《BP2035世界能源展望》,2014年1月,第15頁。
[3]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Data Tables A1: “World tot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by region, Reference case, 2009-2040”, (上網時間:2014年11月9日)
[4]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 November 12, 2013, p. 197.
[5] 吳旻碩:《能源轉型呼喚大戰略和好政策》,載《人民日報》,2014年8月5日,第23版。
[6] 《油價下跌,幾家歡喜幾家愁》,《參考消息》,2014年10月17日,第4版。
[7] 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2013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概述及2014年展望》,載《國際石油經濟》,2014年第1期,第35頁。
[8] 美國環境保護局網站,(上網時間:2014年11月15日)
[9] “Global Carbon Budget 2014”, September 21, 2014, (上網時間:2014年10月20日)
[10] 《習近平:積極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上網時間:2014年6月20日)
[11] 《李克強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家能源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網時間:2014年4月27日)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點擊進入“全國黨建期刊博覽”